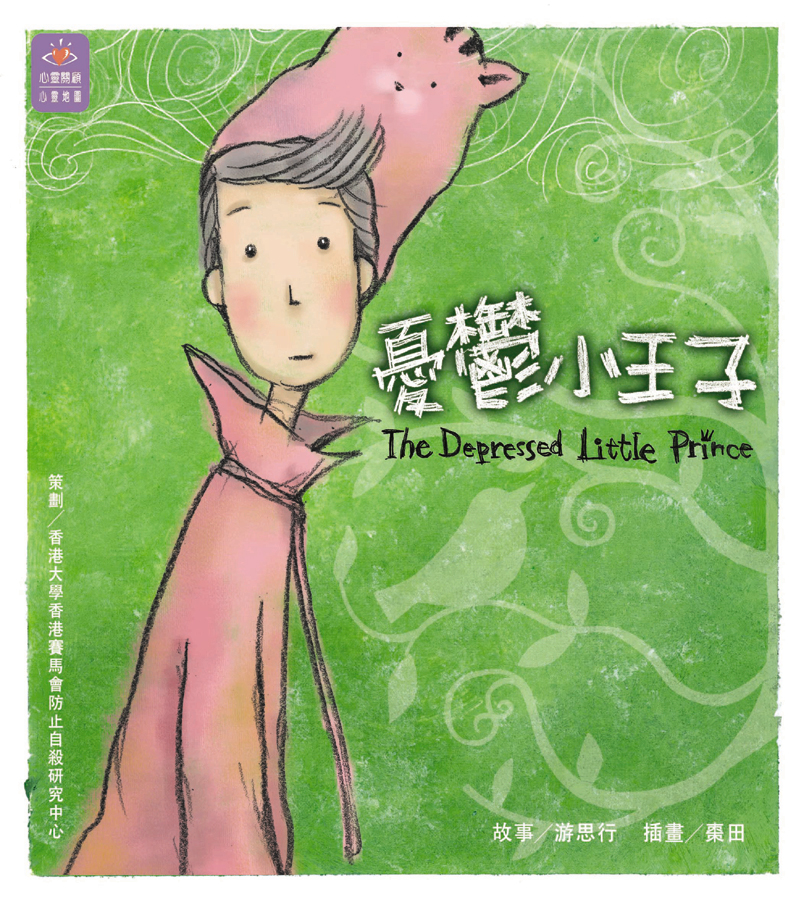Velázquez《Mariana of Austria》1652

《Las Meninas》有一種不能被仿製的竅妙,原畫中有一面鏡子,反映了國王伉儷朦朧的倩影,當你站在畫前,理論上國王伉儷就站在你身後。於是Prado館方 很聰明地分別放置了兩幅也是Velázquez繪畫的國王伉儷的肖像,在《Las Meninas》的正對面,恰好為畫中的鏡子延伸出一個合理的空間。
當觀眾都擁蔟著《Las Meninas》一如小公主的僕人,我卻被王后的肖像吸引住,看著她那個納悶的表情,直至脖子痠痛起來。
肖像中的Mariana王后那時只得十八歲,但已下嫁她的舅父國王Philip四世達四年,她原先是許配給王子,但王子和前王后都相繼去逝,國王後繼無人,就娶了十四歲的她。
這是很典型的西班牙皇室肖像畫,她穿著極其華麗的深黑大罩裙,束著細腰,兩臂被大傘裙撐著必須擱兩旁,頭上紮滿誇張的辮子,還夾了一條巨型的羽毛尾巴,益發襯得臉兒小小的,並不顯美麗。她看起來脾氣不大好,帶著皇室的傲慢,沒有笑的意思,嘴角隱若朝下,不太耐煩的樣子,也許長時間為畫家造像,脖子亦有點痠痛僵硬了,只不過不動聲色而已。
Velázquez《Coronation of the Virgin》1641-44

其實王后又沒有得罪我,我為什麼一口咬定她不美呢?實在是因為Velázquez畫過真正的美女,他所畫 的聖母馬利亞可以說是典範,在《Coronation of the Virgin》(1641-44)裡,馬利亞垂著眼簾,多麼柔美,他很真實地把西班牙少女那種像水果一樣鮮嫩多汁的感覺畫了出來。
王后的臉本該也是少女的臉,理應有著一樣的顏色,她的胭脂與髮上的蝴蝶結屬同一色系,這種嬌嫩的紅色其實很適合她。她兩只腕上也戴著這樣的蝴蝶結,我注意 到她的手很小,拿著白手絹,略為調節了巨大黑裙的壓迫感。但她整個人只露出了小小的一張臉和兩只小手,裙子下的身體彷彿不太真實。
Velázquez《Prince Baltasar Carlos as a Hunter》1635-36(上)
《Queen Isabel of Bourbon Equestrian》1634-35(下)
王后的裙裾點綴著細緻的銀線裝飾花邊,還有頭上那頂毛毛尾巴中的 紅色部份,畫家都用很跳躍的筆觸處理,輕鬆得有點難以置信。法國印象派大師Manet在二 百年後到訪西班牙時發現畫家的作品,他寫信給他的畫家老友Henri Fantin-Latour,信裡讚美著Velázquez是畫家中的畫家,句子斷續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,然而字字透露著一種戀愛一樣的帶點迷惑的喜悅, 自此掀起了法國印象畫派浪潮。此前,畫家的畫一直靜靜地待在皇宮裡,無人知曉,是西班牙最美麗的秘密。
畫家是國王最鍾愛的宮廷畫師,自從進了皇宮就一直待到死那天,大半生都為國王及他的王親畫肖像。這批沒落的皇室成員中除了那早夭的王子,沒有一個是美麗的,但畫家依然有本事化腐朽為神奇。看著那些王親國戚穿著全套厚重繁瑣的華衣騎在馬上,眉梢眼角盡是威風,誰能不厭煩呢?

但連這最無聊的狩獵造像他也繪得 極之生動,叫人無話可說。
據說國王很會品味,喜愛美食、女色、藝術及狩獵,王后後來又很會花錢,西班牙皇朝就在戰爭中衰敗;一如那襲華麗的黑裙子,包裹著被隱藏的、蒼白的、未成熟的身體。
原刊於2005年2月《萬象》(第7卷第2期)〈Prado的金枝玉葉〉,之二,待續。